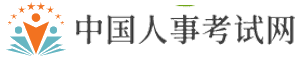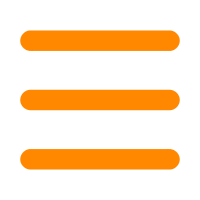1、“友爱的政治”与“敌友之分”
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的《友爱的政治》中说,1927年有两本要紧的经典著作问世,一本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另一本就是施米特的《政治的定义》。 同为经典著作,两者后来的命却迥然不同。《存在与时间》已稳稳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第一经典;而《政治的定义》则在其问世后的六七十年间,渐渐从西方主流学界和常识大家的言谈中销声匿迹,仅仅在一些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的读本中才能看到这篇经典之作。1985年这位97岁的德国大师赫然仙逝。出人意料的是,施米特却在谢世后奇迹般地飞速重回二十世纪西方大师级思想家之列,其在德国和美国两地急剧上升的势头让人暴跌眼镜,连当世大哲德里达也加入到对施米特的追逐与挪用之中。施米特的幽灵开始在美国和欧洲游荡。
然而,与施米特不同,德里达试图形解析构“友爱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友爱”对存在和自然之爱的迷恋及其简单的友爱的政治;因此他也在解构政治,解构那种自然一同体的封闭的友爱政治。德里达以由他者和以后而来的责任和正义之名,试图打造一种承认与尊重差异的无限友爱的民主和无限民主的友爱。施米特在《政治的定义》中所说的“敌友之分”正是德里达的“他者的哲学”要解构的靶子。 对德里达来讲,敌友之分的友爱政治将为差异的“承认的政治”所取代。由此,解构主义者不再是为了无限的能指的差异而汗流浃背的解构运动员,他将成为“无限异质性”的“将来的民主”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在德里达看来,施米特的政治的定义实在“太古典”了,德里达用列维纳斯的“他者”和“无限”的定义及其责任伦理学给施米特的“敌友之分”施洗。然而,从施米特的视角来看,假如取消了“敌友之分”,特别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敌友之分的话(用德里达的话来讲就是取消了“作为他者”的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状况”),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的区别与国家、主权、战争和敌人等定义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其实质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或者“责任”、“将来”、“正义”等名义消除政治,或者说,消除“伟大的政治”。
2、“非政治化的年代”与“政治的定义”
然而,政治是人的存活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精神与精神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生命与生命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存活与存活的斗争的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因而是永远不可消除的。非常重要的是,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存活的基本范围,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的存在方法,是一个政治统一体的首要条件。“以为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便只有朋友,极其愚蠢;设想敌人可能能由于没遇见抵抗而大受感动,则无异于精神错乱。譬如说,无人会相信,假如舍弃所有些艺术和经济生产,世界就能进入一种纯道德的境界。大家更无从期望,假如逃避所有些政治抉择,人类就能创造出一种纯道德或纯经济的情况。即便一个民族不再拥有存活于政治范围的能力或意志,政治范围也不会因此而从世界上消亡。只有弱小的民族才会消亡。” 觉得政治会消亡,国家会消亡,战争会消亡,斗争会消亡,在施米特看来都是“非政治化”年代的谵语,若不是为了别有用心地骗人,便是愚昧无知。因此,施米特觉得要在一个“非政治化的年代”重申“政治的定义”,与政治作为人的“极端状况”或者说“人的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誓死批判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技术化、规范化、道德化、经济化、和平化,一言以蔽之,“非政治化”。
施米特的《政治的定义》的“文化批判”与海德格尔、恽格尔、卢卡奇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是对技术化年代的批判,特别是对技术化年代中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理论的统治地位及其非政治化后果的批判。 施米特对西方现代性独特的历史诊断为他的末世论的调子提供了一副鲜活图景:这是一个中立化的年代,这一年代是西方四百年现代性的伟大变革的结果。西方四百年的现代性是一个剧烈的世俗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分四个阶段:十六世纪的神学,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信念,十九世纪的经济。无休无止的神学争论和宗教斗争使西方从十六世纪开始探寻用技术方法消除冲突的中立化范围,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开辟的中立化范围成为重心不断转移的新的斗争范围。中立化的进程致使了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信念对人类的主宰和控制。“今天,工业化国家的大众仍然依从于这种麻痹人民的宗教,由于他们像所有大众一样,寻求各种激进的结论,而且下意识地相信,大家可以在此找到追求了四个世纪之久的绝对非政治化,常见的和平便从这里开始。但,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二者的机会相同,此外,技术什么也办不到。就此而言,无论是以和平的名义讲话,还是借助和平这种不真实的套话,都不可以改变什么。今天,大家已经看透了,大众建议的心理-技术机制怎么样借助各种名目和言辞的迷雾来运转。今天,大家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方法,知道了大家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最后,大家也看清了那一代人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技术年代精神的死亡与没灵魂的机械论。”
施米特的“政治的定义”既是针对着四个世纪的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世俗化,也是针对作为其后果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技术化政治。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不只进步出“管理而不统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定义,不只在大革命后进步出私生活活的审美化和浪漫化的范围,而且二者在政治的技术化、中立化和自由化的整理之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浪漫主义”,如缪勒和施莱格尔之流。政治浪漫主义和技术化的政治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国家成为法律秩序,而法律成为“国家理由”。然而,对于施米特这位欧洲数一数二的公法学家来讲,宪法学说要从国家的统一体及其主权来理解; 而在这位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政治学家看来,国家的统一体及其主权要从“政治的定义”来理解。“在法律生活的日常,至关要紧的是由哪个来作决断。权限问题一直与实质的正确性问题并驾齐驱。法律形式问题就存在于决断主体与决断内容的对比中与主体的正确含义中。它没先验形式所具备的先天性空洞,由于它完全产生于法律的具体性。法律形式更不是技术性的精准形式,由于后者具备要达到某种目的的功利性,它在本质上是物质性的和非人个性的。最后,它更不是审美商品的形式,由于后者对决断一无所知。” 施米特的“政治的定义”,从常见的意义上来讲,是对技术化、中立化、非政治年代的批判;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讲,是对议会民主、形式主义法学、国家与社会的离别与自由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理论的批判,特别是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
3、“自由的技术”与“威权的政治”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被当今的自由主义者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最大推进。当今西方最热衷施米特理论的乃是那些自由主义者。施米特在“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年代环境中复兴,这一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施米特目光如炬,他深刻地看到自由主义没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只有从伦理和经济对政治进行批判;没国际政治,只有国内政治或政党政治。“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与对自由的倡导,同样具备某种政治的意思,在具体的状况下,这所有便会致使激烈地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但,这既非一种政治理论,也非一种政治观念。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激进到否定国家,但从其次看,它既没提出一种实质的国家理论,也没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的渠道,它只不过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范围并使之服从经济。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离别和制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和政府的体制。这既不可以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可以被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 施米特深刻地洞见到,自由主义将政治局限于伦理,也即局限于批判国家的专制、限制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的权利之上,并进而使政治服从于经济。他深刻地指出,自由主义以人权的名义抵消了主权,以自由的名义消除去民主;在自由主义那里,没真的的政治的风险和政治的极端状况,也没真的的政治的定义。自由主义从权力、法律和权利、公共事务、国家等角度界定政治的定义,致使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即以行政和治理吸纳并消除政治。然而,政治是永不可消除的,也不可防止;在施米特看来,声称所有些政治和权力都是恶的、因而需要加以限制和消除的学说,假如不是真的的无知,就是有意的欺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没走出两个多世纪前对专制国家和封建贵族的批判性建构。自由主义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最为危险的武器和工具。
施米特试图超越和克服自由主义主流的意识形态。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术年代、世俗化的批判并非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更准确地说,不是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而是从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也即“威权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这就能讲解他为何投机于纳粹的威权社会主义,成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 德国“文化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守旧主义是施米特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术年代、世俗化的殊死为敌,并站在“威权社会主义”的立场的根源之一。
克里斯蒂将施米特视为一个平衡自由与民主、民主与权威的哈耶克式的“威权自由主义者” ,这是一个戴上了霸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眼镜的学者的建议。克里斯蒂觉得施米特的关怀是,对于魏玛民国的市民社会的宪政而言,没权威也没民主的自由是没保障的自由,因而是危险的自由。由于,自由并非一种政制,更不是一种合法性。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自由可以在不一样的政制中达成,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威权的保障中达成;相反,多元论的自由价值观却完全可以毁掉削弱国家的主权并毁掉一个虚弱的国家。克里斯蒂因而断言,施米特的冲动并非反对自由主义,而是加大政治自由主义;这一关怀与韦伯很相似,尽管施米特使用了完全不一样的语汇和批判形式。
[1][2]下一页